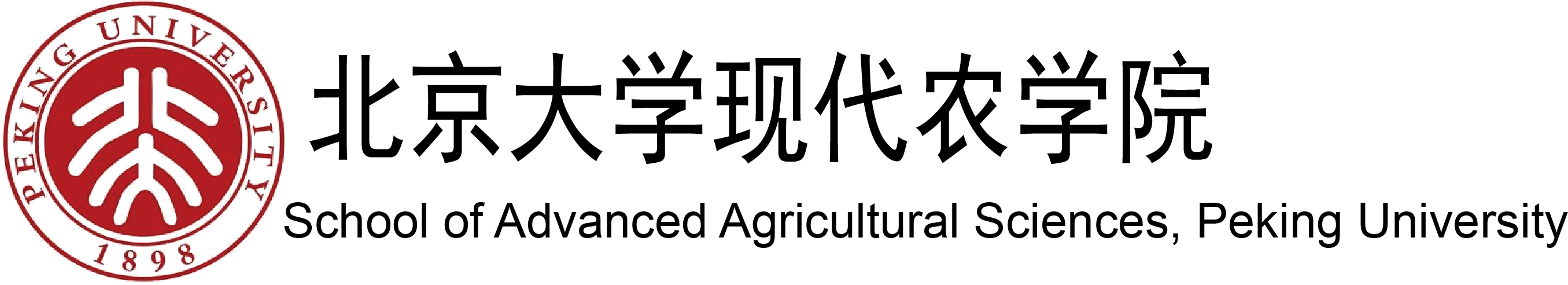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廖洋 实习生 王冰笛
光合作用被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诺贝尔奖曾经8次都颁发给了与光合作用相关的研究。
然而,植物究竟是如何“看到”光,并知道自己何时需要进行光合作用的?
“植物不像人一样通过双眼观察周围的世界,它们直接通过蛋白质感应太阳光。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析了植物如何通过自己的‘眼睛’去感知红光,进而指导光合作用的开启。”一见面,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90后”研究员王继纵就用非常生动的比喻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了他们的工作。
近日,王继纵课题组与同单位邓兴旺课题组合作在Cell发表相关论文,揭示了领域内期待已久的植物红光受体光敏色素B(phyB)光信号转导的最初反应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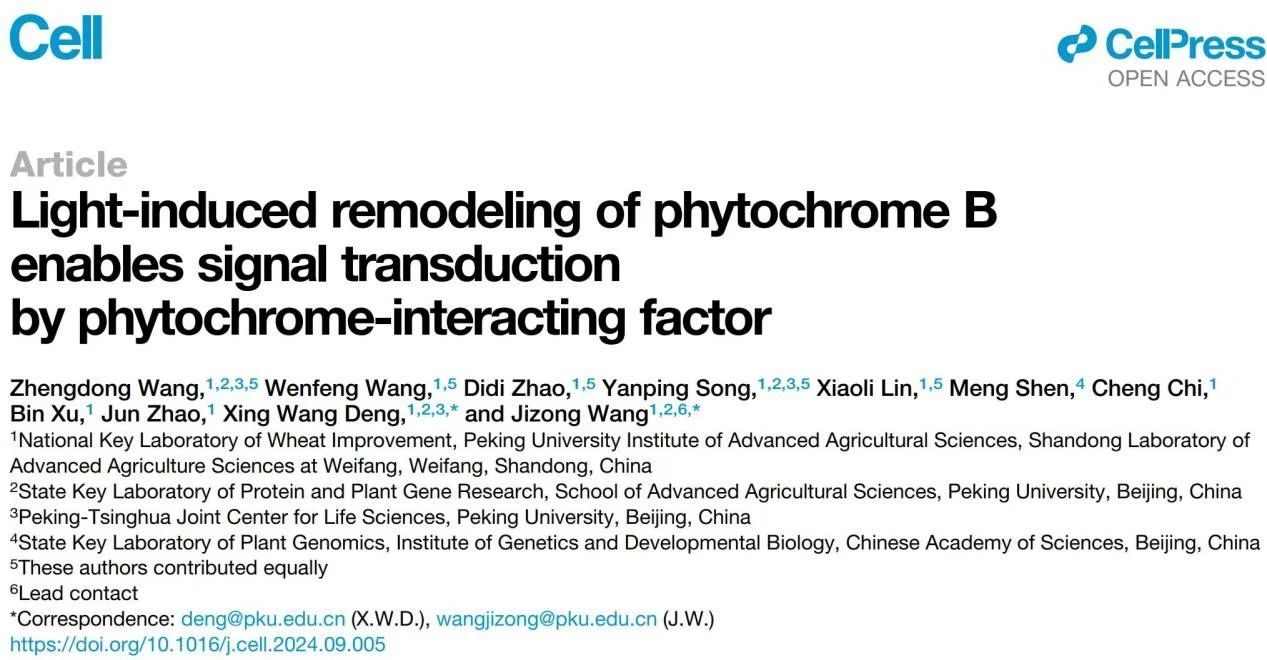
用4年时间解决困扰70年的问题
其实,有关植物“眼睛”的研究,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52年,美国Beltsville农业研究中心的植物光生物学研究先驱H. A. Borthwick和S. B. Hendricks以单色光处理莴苣种子,发现红光促进莴苣种子的萌发,远红光照射则抑制其萌发。
在此基础上,S. B. Hendricks等人于1959年成功地从玉米茎尖中分离出植物感受红光和远红光的光受体——光敏色素,自此开启了植物对红光和远红光感知的研究之路。
1989年,植物光敏色素研究的先驱和权威、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Peter Quail终于在拟南芥中克隆出植物编码光敏色素蛋白的基因,此后开始通过遗传手段研究光敏色素的信号通路。
但是,局限性依然存在,人们始终无法确定植物感受红光“眼睛”的构造。这限制了对其感光机制的准确理解。
2020年7月,王继纵入职北京大学,并带领团队用了一年的时间做相关的实验室体系搭建和筹备工作。
从2021年7月到2022年12月,他们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断摸索,对植物“眼睛”开展纯化和收集工作。

2020年7月,王继纵加入北京大学。
仅仅四年过后,2024年9月,他们就对植物如何看见周围的光线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并将文章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Cell上。
但是,如此迅速获得的成果背后,并非每一步都一帆风顺。
2022年12月,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他们发现,已收集到的植物“眼睛”竟无法正确感知红光!
事实上,植物的“眼睛”需要装配一个有机化合物来充当“视网膜”。而这个化合物的合成过程比较复杂,团队前期一直未能解决其合成与装配环节的问题,使得他们的植物“眼睛”不能看到光。
王继纵苦笑着回忆道:“相当于我们前面两年半的时间里,获得了植物‘眼睛’的主体框架部分,却把最重要的视网膜给搞丢了,我们拿到的其实是‘盲人的眼睛’。”
这一结果,无异于当头一棒!
然而,来不及为结果沮丧,团队继续调整方向,运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光谱学等一系列更严谨的方法反复尝试,攻坚克难。
论文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征东在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先锋角色。
2023年3月至5月,他们终于完成了对植物“眼睛”精细分子结构的解析工作,获得了植物这双“看得见的眼睛”。

2024年9月,王征东在泰山
为什么是他们做成了?
在王继纵团队研究成果出来之前,光敏色素有关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始终都被欧美科学家垄断。
因此,成果发表后,许多人祝贺之余,都在问:“为什么是你们做成了这件事?”
这离不开合作团队各学科的交叉融合。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由北京大学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创立,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邓兴旺担任院长。过去的30多年里,邓兴旺始终利用分子遗传学为主的手段解读植物光生物学,王继纵则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和做博后的十年间,一直跟随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柴继杰教授(现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从事植物蛋白与复杂生物大分子机器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此外,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赵珺用自己擅长的冷冻电镜技术与团队研究方向相结合,创新性地改造了实验仪器,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由于植物的“眼睛”是动态的,可以看到红光,但同时对远红光又会快速关闭,而自然界的太阳光是混合光线,非常紊乱,使得研究者难以看到它的结构。赵珺解释道:“所以我们需要对仪器进行改造,让植物的‘眼睛'始终处于红光激活的状态中。”
这个改造的想法,来源于赵珺参观王继纵实验室的亲身经历。
在前期蛋白质收集过程中,为了不让植物的“眼睛”蛋白受到其他光的影响,王继纵他们设置了许多间小黑屋,有些小屋只架设绿光,有些只架设红光。
赵珺看到后非常疑惑,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光源?王继纵解释称,必须让植物蛋白处于不同光线下的稳定状态,才能研究清楚。
听闻此言,赵珺不禁思索:那么仪器是不是也能做成迷你版的小黑屋,保持光线稳定?
“理论上这样更好,但是改造仪器是否不太现实?”王继纵并没有对赵珺所在的电镜团队提出强制性要求。
要知道,电子显微镜被称为科研领域的光刻机,结构非常复杂,价格异常昂贵。因此,尽管电镜在各研究机构并不少见,但大多数人不敢轻易改造。
做出改造仪器的决定时,有过犹豫吗?“完全没有。”赵珺说。他的导师黄建宇教授是原位纳米电池技术开创者,是第一个把纳米电池放进电镜的人,“他一直都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明白原理,明白以后永远不会搞坏”。
赵珺开玩笑地说,“我的老师们在物资匮乏的90年代都是一群擅长DIY的老男孩,所以他们的学生也敢于改造。“
对老师创新精神的传承,使得赵珺凭借足够扎实的技术能力成功对仪器进行了改造。
改造后的电镜仪器,既能让植物“眼睛”始终处于红光的稳定状态,同时研究人员可以置身外界的正常光环境中进行研究。
这对他们最终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时候,离成功或许就差大胆创新这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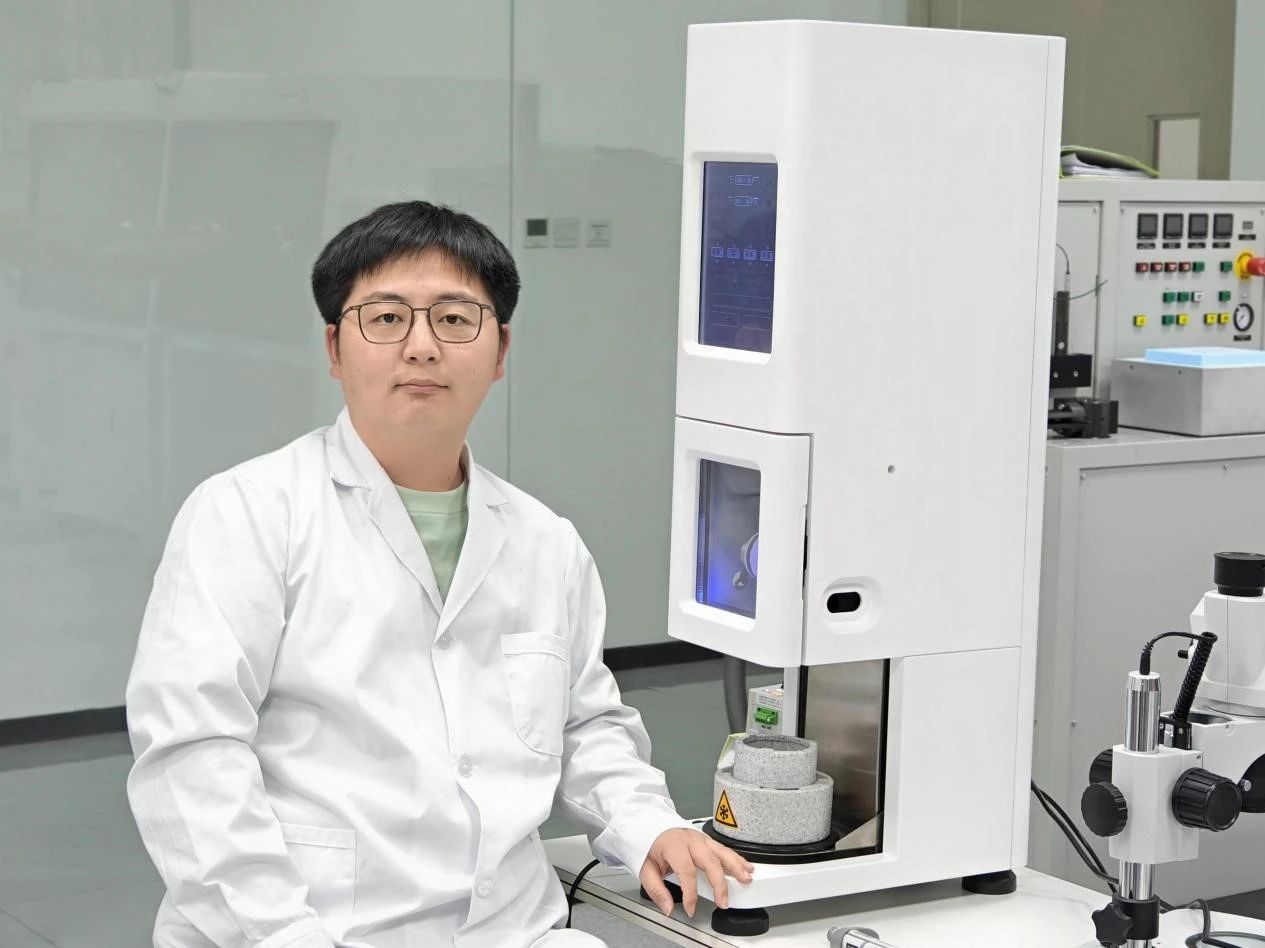
赵珺在电镜室应用自研设备进行实验
5个月发表,这群90后年轻科学家的故事还在继续
尽管研究过程经历了更换植物的“盲眼”、改造复杂精密仪器等关口,但论文的发表环节却十分顺畅,从提交到发表,仅仅5个月。
2024年3月31日,他们提交了论文。五天后,论文第一轮审稿。三位审稿人中有两位对他们的结果感到无比惊讶,认为“这是领域内的巨大进步,将成为植物科学和光遗传学领域一个里程碑事件”。
第三位审稿人则在惊讶之余,对文章提出了一些疑问,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完善一些。
“我们针对这位审稿人的问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详细的修改和回复,有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王继纵说。
但是,当两个月后再次提交修改版本后,仅两周的时间,文章就被原则性接收。
那位曾提出问题的审稿人回复:“我现在完全理解了这个研究的意义,报道激活状态的红光受体结构的确是光生物学里的重大突破,以后整个红光受体的研究历史将以此分为‘结构未知’和‘结构已知’两个纪元。”
文章出来后, Peter Quail和他的夫人、德国科学院院士Katayoon Dehesh欣慰地说:“非常兴奋能看到领域内这个重要问题有了最终的答案。”
德国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教授、植物光受体分子结构研究先驱Jon Hughes同样对他们的研究表示非常赞赏。
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届全国植物光生物学大会上,该成果得到整个光生物学领域专家的认可与祝贺。
取得如此成绩的背后,是一群“90后”科学家们日复一日的坚持。
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有时候一个实验阶段要经历十几个小时,且不能中途停止。因此,王继纵常常向学生们强调做科研一定要严谨、有耐心,让“每一个实验结果都能经得起反复推敲,这也是节约时间的一种方式”。
他常常鼓励大家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每周都会有学生负责订场地,大家约在一起打羽毛球。
而对于赵珺所在的电镜团队来说,他们的工作也十分辛苦且重要。“仪器的单台价格需要几千万元,因此我们需要按照它的时间去配合,像照顾孩子一样去维护。”
有时电镜半夜出故障,他们要立马赶到现场维修。做实验的学生们着急需要数据,他们也轮流值班彻夜陪伴大家。
提起电镜技术的发展,赵珺说:“目前科学仪器都非常昂贵,并且长期被国外垄断。想要打破这一局面,需要让更多交叉学科背景的人走到一起,汇聚在十字路口,完成原始创新。”
他希望能将自己的电镜技术和仪器开发经验应用于更广阔的交叉学科领域,用国产前沿仪器支撑更多本土突破性研究。
王继纵出生于1990年,赵珺则是1993年。两位年轻的“90后”科学家,始终不忘报效国家的初心。
王继纵坦言道:“希望能尽心尽力,将这个领域做得更完善,争取使国家在该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

今年9月团队成员在泰山的合影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4)01023-7